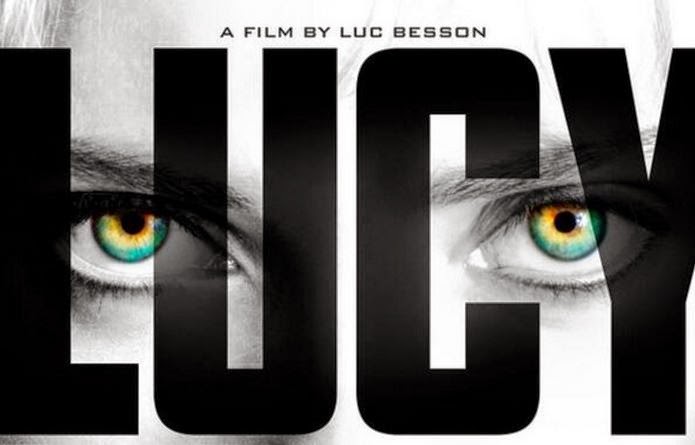日前,手痕在日式超市購買試酒卡,飲到一款叫Vin de Constance的南非Klein Constantia葡萄園甜白酒Natural Sweet
Wine,在販賣機酙放鼻前,好複雜的花果香味,更更一點似陳皮或乾果皮之類香味,俺這名葡萄酒大鄉里又真的從來沒有接觸過有如此複雜香味的葡萄酒,一啖進口,嘩!更加不得了,當下知道找到俺心中的「神之水滴」了。對此酒一無所知下,只知道店員哥哥謂必須開栓醒酒起碼3-5小時,抱了此500ML神酒便去居酒屋飲,眾讚口不絕,一酒友之弟,什懂葡萄酒,一看到FB中相片,即留言謂何人懂貨找來這支拿破崙臨終前尚想品飲的酒。咦!似乎此又是一瓶物語纏身之酒。
回家上網一搜,原來豈止 拿破崙臨終前尚對此酒念念不忘,此南非出產的Constantia甜酒一身傳奇,俺只好節錄:
「其實自17世紀末在不少人的遊記裡就提到,但到18世紀尾熱潮才爆發,在19世紀初期歐洲皇室把他視在Yquem,
Tokay 和 Madeira之上,國王們個個想盡辦法取得,法國國王Louis Philippe曾經派專使特地去把酒運回,拿破崙最失意時在St.
Helena 島上喝的也是Constantia,德國的Frederick the Great 和 Bismarck 和英國國王總理們也都是愛好者。英國的名作家Charles Dickens 和 Jane Austen, 德國和法國詩人都曾經在作品裡讚賞過這一款酒。奇怪的是這種從開普(南非開普敦地區)取來的葡萄藤母株種在伯恩區(法國勃根地地區)與鄰近葡萄園生長都不理想,只有在開普敦才生長茂盛。原因乃沒有辦法把陽光跟泥土取回,可見當時在歐洲有多少人想要複製她。
在18世紀英國對有進行交易奴隸的港口進行封鎖,
1861年開放法國酒進口,南非酒在英國的優勢消失,
1866年遇到phylloxera(葡萄根瘤芽蟲病)後整個南非葡萄酒業進入黑暗期,
1885年Cloete 家族把葡萄園賣給政府作研究農場後葡萄園部份就被荒廢下來,
vin de Constance 有著深黃色的色澤,俺品嚐2008年份釀造的,女酒友弟弟手上有3瓶1998年的,聽到都吞口水,她答允取一瓶來分享,到時便知陳年的是否更加複雜香醇。而日本清酒中大吟釀級酒的任何花果上立香和任何高級儲藏酒的醒酒後所散發出來的香味,看來都要靠邊站了,委實白米釀造的酒是不容易走到這一步,俺是明白的,所以現代藏人和杜氏已經花了不少心力去改造清酒,希望在國際酒市場中佔上一席位。
回說vin de Constance,俺覺得如在飲超級拔蘭地,但又少了俺討厭的拔蘭地那股藥材味,因為俺味蕾記憶中抹不去兒時偷飲家中珍藏陳年跌打酒,以拔蘭地浸阿爺從美國印地安人手上買回來的草藥,那味道如中了毒,以後一見到拔蘭地,就是那股藥酒味道,所以當人人都喜歡牛飲拔蘭地的時代,俺卻去飲威士忌,但威士忌則迄今未能接受其中一系列的泥煤味,太跟牙醫藥水味道相像了。飲酒都是飲到合適自己所喜愛的味道比較愜意,其實也毋須跟風隨流,一切找尋在嚐試,飲者亦享受此過程。
而到今天終於有點理解何故酒齡甚長,品酒甚多,藏酒量更是驚人的名作家 Evelyn
Waugh(註2),在晚年口味卻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對波爾多五大酒莊點滴不沾,只集中飲平價的智利、德國紅酒,還四處向人推薦葡萄牙的玫瑰紅酒 Mateus Rose(碼頭老鼠)了。他沒有精神失常,可能只是找到飲葡萄酒真正意思,進口爽快好味又夾任何食物,最後不傷荷包便能買一場醉。而vin de Constance都只是半張一千元以下的價錢,是否因為其南非出產,又屬冷門的餐後甜酒類而被香港市場忽略呢?
其實vin de Constance拿來全天侯飲用都可以的,一頓西餐或西班牙TAPAS先來Mateus Rose,或者日本餐先來一些好的新世代清酒,然後皆再來品飲早已開栓的vin de Constance,那已經是前生修來的福份了吧。
酒之味道,俺悉性不崇尚高深,人生苦短,那只好相信自己天賦的舌頭來找尋,「脷酒師」也不是浪得虛名,今回一於老鼠跌落天枰。準備找心愛的Constantia去也,其實是酒找人,冥冥之中似乎一切自有奇妙安排。
俺估不到在本欄臨別時刻 ,遇上了心目中的「神之水滴」卻是反高潮地完全跟清酒無關。也在9.28見到久違了三十年首枚射向香港人的催淚彈,也在灣仔酒吧飲啤酒時,見到街頭外幾十名手持長鎗指向四周的防暴警察,更指向一名市民頭,被大量市民高喊停手後,臨退回敬出一枚催淚彈,菲藉酒吧員工、英國遊客,香港人客,同聲一「WHAT THE FXXX !」,再無心飲酒,只互道「TAKE CARE」黯然而散。
下周二便是《酒藏浪客》暫別篇,敬請看倌備酒,邊飲邊看,更到喉肺。
(註2) Evelyn Waugh《故園風雨後》作者